转自:法纳刑辩
来源:刘哲说法
作者:刘哲
判决要在生效之日起执行,这不仅是常识,也是法律的明确规定。
因此不仅是缓刑,事实上无论任何的刑罚,都不能在判决尚未生效之前执行。
但是刑事诉讼法确实有一个特别的规定,那就是第260条所规定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免除刑事处罚的,如果被告人在押,在宣判后应当立即释放。
从日常的感官来看,当庭释放也几乎就相当于判决的立即执行了,虽然这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执行。
很可惜的是这个条款并未包括缓刑,这很可能是因为,无罪和免刑就意味着不用执行任何的刑罚,因此也不要太多的交接手续了,可以比较干脆的当庭释放。而缓刑还是需要进行社区矫正的,而一个还没有生效的判决是无法交接的。
而且既然判决没有生效就意味着还存在变数,如果检察机关抗诉,经过二审就有可能改判实刑,那也就不存在社区矫正的问题了。
事实上,无罪和免刑也存在一样的变数,但是法律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考虑,还是要坚决的释放,即使二审之后可能有无罪变成有罪,从不用服刑到需要服刑,到那个时候再说。
也就是法律在保障诉讼顺利进行与保障人权的天平上,向后者进行了倾斜。
那缓刑是否可以获得相同的待遇呢?
在司法实践中,判决缓刑时一审法院近乎惯例的会为其取保,从而也会产生一个当庭释放的效果。虽然这并不是法律规定的当庭释放,但实际上的效果几乎是一样的。
但依据是什么呢?
这个依据法律上是找不到的,其来源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这个条款从1998年就有了,到了2021年也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以最新的条款为例,就是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单独适用附加刑,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应当立即释放,必要时,可以依法变更强制措施。
这个变更强制措施的规定在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措施的规定中也没有,而这个关于释放的规定也不是规定在刑罚的执行当中,而是规定在强制措施部分。
更奇怪的是,这一条解释的规定,基本上从1998年沿用了2021年,沿用了23年,但至今也没有为刑事诉讼法所吸收。
刑事诉讼法关于未生效判决的释放只限于无罪和免刑,而司法解释又扩展为缓刑、管制、单处附加刑,后续的条款还扩展到被告人被羁押的时间已到第一审人民法院对其判处的刑期期限的,案件不能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审结的。
这实际上相当于对刑事诉讼法的释放条款进行了扩大的化解释。
这个解释显然是有利于被告人的,也为司法实践中普遍的接受,因为认为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只是很多人不了解其真实的出处。
所以缓刑判决虽然不会真的被立即执行,但是判处缓刑的被告人真的会被立即释放。这是一条一直不被立法正式承认的司法解释所规定的。
既然这个条款是有利于被告人,有利于人权保障的,为什么刑事诉讼法会冷漠的忽视二十多年,法院也坚持了二十多年呢?
这是因为刑事诉讼法已经放弃了这些诉讼制度细节的规制,它认为这是一个细枝末节,无需法律制定或者完善的一个条文,而且也并没有因为这个条文的不完善而产生什么事端。只要不出事,就可以维持这个以刑事诉讼法为基本框架,以两高司法解释为延伸空间的刑事诉讼制度规制体系。
刑事诉讼法实际上放弃了程序法定原则,比如关于何人可以在判决生效之前当庭释放的问题,单位犯罪诉讼程序的问题,核准追诉等程序,几乎放弃了规则的制定权,可以听凭司法机关自行规制。
司法机关在没有刑事诉讼法条文基础,或者基础有限的情况下的程序设计实际上就发挥了立法功能。
而刑事诉讼法对此并不排斥,对其吸收也并不积极,从而形成了一种程序法规则的松散体系,与刑法与司法解释构成的紧密体系有着显著的不同。
回到缓刑执行上来,缓刑也好实刑也好,毕竟是没有生效的判决凭什么就可以优先执行?
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这是否对判决生效执行的一般原则构成了冲击,破坏了法律的权威?
这里边有这么几个考量:
01
判决缓刑时,如果仍然羁押的,如果不立即变更强制措施予以释放,就意味着要延续羁押状态。而这种羁押状态实际上就构成了一种实刑的实际效果,这是与缓刑的判决直接相冲突的。
02
如果后续再有二审程序,只要不改变措施,就会被一直被羁押,这个诉讼时间如果长达数月或者一两年,那可能就比判处实刑的刑期还长,这是对被告人的一种不公平,诉讼本身构成了一种惩罚。
03
迟到的正义为非正义。无罪、免刑当庭释放的意思就在于一刻不能耽搁的执行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让正义这个感受最大化。这不仅是对被告人有正面的影响,对被告人的家属和公众也有着正面的影响和教育意义。
因为很多无罪判决,几乎都意味着冤错案件,这种案件拖延执行不仅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实现,而且容易激起民怨,形成与公众朴素正义观的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判决还没有生效,先把人放了,也是值得的。而且这样的案件毕竟是少数。
缓刑也有一些相似的道理,但理由没有那么充分,主要也是让被告人得到正义最大感受,让宽缓的处理决定能够立即兑现。
但是确实与无罪这种公信力、朴素价值观、公众舆论考虑等还是有所区别的。
但是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对缓刑所带来的这种自由的不耽搁,也能够体现司法机关把人当回事的态度,这虽然对生效执行上有冲突,但总体上还是说得过去的。
当然立法一直没有正式接纳这种扩大的立即释放权,是不是对这种冲突还有所犹豫,目前并不明朗。
而且还有,在取保候审立即释放之后,缓刑执行之前,这段时间实际上存在一个风险期,也就是还存在一定失控的可能性,比如在送社区矫正的时候,联系不上人,手机关机了。以为自己没事了,换手机了,回老家了,这也是非常麻烦的。虽然看起来保障了人权,但可能会以刑罚执行不能无缝衔接,导致缓刑无法有效执行的风险依然是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立法迟迟没有接受可能也有更加慎重的考虑。
另外,从相反的角度看,非监禁刑的立即释放,也就是变相的“立即执行”,是不是使监禁刑不能立即执行就显得好像有一种不公平。就比如虽然是取保状态的,但判处实刑的,就需要生效后才能执行,而取保状态是不能折抵刑期的,这就意味着诉讼时间就成为消耗,不管折腾多长时间,最终还是要从头服刑,这就使诉讼期间成为一种煎熬,想要立即服刑也做不到。
是不是不上诉,或者没有抗诉,就可以不用煎熬呢,有时候由于特殊时期公共卫生的考虑,也会被耽搁,比如看守所就是不受,你就进不去,进不去就服不了刑,服不了刑,这个事就总是没完。虽然刑期很短,但也会产生一种没完没了的感觉,这也会导致一种新的不公平。
因此,我们在考虑立即释放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些可以立即服刑的相应快速处理机制,从而实现一种平等保护。
在平等保护上,绝不仅仅是一个释放的简单处理方式,不迟延地执行,实质的考虑当事人的利益,并兼顾公众的正义观感是需要司法机关考量的现实问题,也是立法机关不能忽视的重要程序内容。
程序法定的基本原则决定了程序设计绝不仅仅是单个司法机关自行的利益考量,必须经由立法机关从全局角度进行认真权衡。程序规则体系应该由松散体系逐渐向紧密体系转变,要进一步强化刑事诉讼法在诉讼程序设计的核心权威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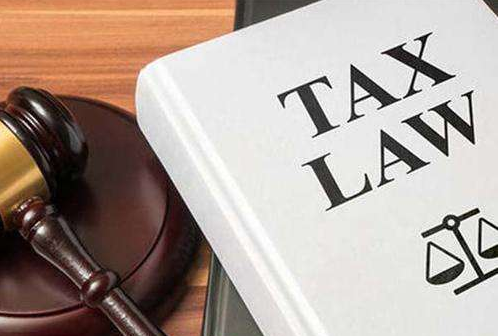

发表评论